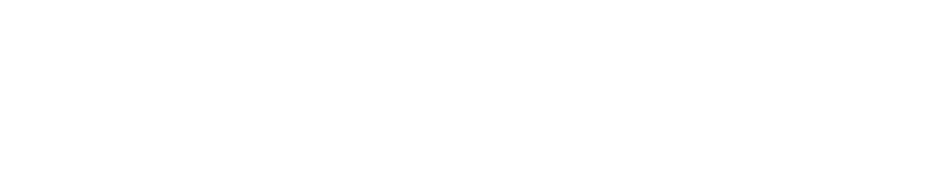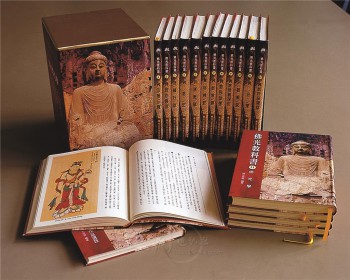貧僧有話要說二十一說之三 我一生「與病為友」
之後,身體陸陸續續都有一些況狀,幾乎每年都要進出醫院幾次。像一九九八年十月,因為糖尿病血管硬化的併發症,侵蝕了我的心臟,也侵蝕了我的雙腿,讓我不良於行。在信徒趙元修夫婦的建議下,到了美國休士頓美以美醫療中心(The Methodist Hospital),由八十多歲高齡的狄貝克(Dr. Debakey)醫生,為我進行頸動脈血管阻塞疏通手術。在醫師嚴正囑咐下,手術後一個星期,我便到澳洲黃金海岸佛光緣中心閉關休養。
貧僧想,做一日和尚,撞一日鐘,於是在閉關的時候,帶著書記們做《佛光教科書》的撰寫編輯。雖然身體不良於行,還有嘴巴可以宣說佛法,也就一心一意地指導他們編寫這一套書,希望讓佛教徒有修學佛法的課本可以研讀。
因為糖尿病久了,影響到眼睛視力模糊,右手顫抖,將近二十年前,就在台北請醫師為我做眼睛鐳射治療。那時候,老舊的機器替我的兩隻眼睛打了三百多下,不見好轉反而惡化。由於經常往來美國弘法,洛杉磯有一位旅美眼科名醫羅嘉醫師,醫術高明,他也為我鐳射,打了一、兩百下都沒有聲音。在他悉心治療之下,我維護住了眼睛,戴上眼鏡矯正,勉強還可以看。
一九九九年,七十三歲的我,視力日漸退失,曾經也給國內眼科權威文良彥醫師看診,他告訴我:「在醫界服務二十多年來,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糖尿病患者,在接受多次鐳射治療後,還能保有像你這樣的視力。」他這樣的一句話讚歎,貧僧也感到有些安慰。
後來到了美國,因為眼睛再度出血,在當地,羅嘉醫師又一次為我診療雙眼,並且進行鐳射止血。他如實的告訴貧僧,生病的眼睛,就像是一件破舊的衣服,破了縫補,只會再壞,並不會變好。他要貧僧對還能用的眼睛,多給予愛護,讓他多休息,讓僅存的功能,維持最好的狀態。
為了這雙眼睛,承蒙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的關心讓我到北京看診,那許多老醫師也給我很多醫療的意見。也承蒙美國邁阿密一位信徒,特地把醫療儀器搬來台灣為我醫療,他不相信不能為我醫好眼睛。但是洛杉磯沈仁達醫師告訴我,糖尿病是不會好的,等於頭髮白了,還會變回黑髮嗎?他的這句話,等於宣判了我那一雙因為糖尿病而引起病變的眼睛死刑。從此以後,貧僧也不太去在乎它了。
後來,由於眼睛退化很快,又加上眼底鈣化,幾年前開始,有人站在前面,貧僧可以知道前面有個人,但是人的五官長什麼樣子,已經看不到了。不能看書,不能看報紙,做什麼好呢?忽然想到,可以寫字。憑著心裡的衡量,一筆到底,不能中斷,因為只要中途停頓,第二筆要下在哪裡就不知道了,所以叫它「一筆字」。這也算是貧僧與病為友另外的一種成長,雖然身體的功能一直在降低,但貧僧也不以為苦,總是在生活中,創造自己的價值,學習做自己的貴人。
二○○三年三月,貧僧因為膽結石發炎引起劇痛,連夜住進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室,因為高血壓一直降不下來,在醫護人員陪同下,又至台北榮總,由雷永耀副院長親自操刀,為我割除膽囊。記得那次,我還在每年寫給護法朋友的一封信裡寫下:「……從此,我已是『無膽』之人了,雖然生命去日無多,但在這個複雜的人間,還是『膽小』謹慎為好。」
二○○四年,我這個雞皮鶴髮之軀,視力比起以往更加不及。八月,在美國弘法期間,右眼確定患有白內障,又由羅嘉醫師為我進行水晶體置換手術。
二○○六年四月初,我不慎跌斷三根肋骨,雖然已是耄耋之年,強忍著連呼吸都痛的傷勢,按照既定行程,應邀前去浙江杭州參加首屆的「世界佛教論壇」,並且進行兩個小時的「如何建設和諧社會」講演。
貧僧的堅持,讓身旁的弟子擔心不已,但一想到自己多宣講,可以促進兩岸來往,對未來宗教、文化、種族的和諧共融,能夠略盡棉薄之力,也只有義無反顧的向前去了。因為貧僧自小從戰爭中走過來,知道戰爭的悲慘可怕,兩岸人民同文同種,不可以再有戰爭啊!
同年十月,因為要飛往印度海德拉巴市(Hyderabad)主持皈依典禮,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醫師不放心,就在他的陪同下,我帶著心律不整,和隨時會有心臟衰竭之虞的色身,前往參加「安貝卡博士(Dr. B. R. Ambedkar, 1891-1956)五十周年的紀念會」,同時主持二十萬人皈依三寶典禮。
二○○七年四月,我又因為一時不小心,造成手腕骨折斷裂。俗話說「傷筋斷骨一百天」,在長庚骨科郭繼揚醫生及復健科吳宜華治療師的協助下,將我的手固定;而那三個月,讓貧僧學習如何使用一隻手生活,也算是生命中一次獨特的體驗了。也因為貧僧常常頭暈,自然要跌倒,因此跟徒眾們自嘲說,我對跌倒很有經驗,懂得如何跌倒,不會受傷太大,要他們放心。
除了這些大一點的毛病,小毛病也不是沒有,就常有人要介紹什麼醫生、什麼偏方。台灣南部有一位名中醫,每天門診都有大排長龍的病患等候診治,但這位中醫師對貧僧有特別緣分,常要上山來為我治療,我都婉謝。胡秀卿女士是台灣女中醫師公會的理事長,因為她從幼年信佛虔誠,看到我熱心弘揚佛法,主動要做我的隨身護理,但我不覺得有這個需要,所以也拒絕她的好意。
貧僧不會去聽信別人有什麼偏方、辦法,或者什麼特效藥,但確實自己也有一些方法去對治一些毛病,例如:香港腳、痔瘡、暈眩、感冒、止癢等。但在這裡不方便公開,因為個人有個人體質的反應,在這個人適用,在那個人可能就不適合了。光是感冒,就有千百種的病菌引起,哪裡能人人都適用的呢?
像有一次,貧僧應邀到基隆做一場講演,因為感冒,咳嗽不停,一位信徒知道了,自稱有特效藥,可以一針見效。我雖然不喜歡打針吃藥,礙於演講在即,也不喜歡拒人於千里之外,就答應他了。哪裡知道,這一針打下去之後,膀子竟然舉不起來了,連脫衣服都困難,只有忍耐,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,才漸漸好轉。掛念這個信徒會被人責怪,也一直不敢說,至今這個信徒是誰,我都不敢告訴別人。
後來,一位醫生告訴我,傷風感冒不用吃藥對治,只要多休息、多喝水,就可以痊癒了,坊間一些感冒成藥,只是心理的安慰,實際上沒有多大療效。因此,有人要給我吃什麼秘方、偏方、補藥,我都只有謝謝他們的好意了。在我認為,任何疾病臨身,要先檢查原因,再給醫師治療,唯有正知正見,以正確的方法面對才是最重要的。
而對於有些年輕人的觀念,我也很不了解。常常身體有病了,南部不看,一定到北部看,北部不看,非得要到南部看;或者是西醫不看,指定要看中醫;中醫不看,也一定要看密醫。其實,為了健康著想,看醫生還是要慎重一點才好。
說起我這一生與病為友的經驗,很感謝早期佛光山大專佛學夏令營的學員,他們當中,有一些人後來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做了醫師,像美國的沈仁義、李錦興、鄭朝洋,日本的林寧峰等,我在各地弘法、建寺,牙痛、眼睛、皮膚等小毛病,都經過他們悉心為我治療,也沒有什麼大礙。
所以,我的「與病為友」的想法,覺得很有用,大病,不會來找我,小病,只要對它稍微關心一點,也不致造成什麼大害,大家相互尊重,就這樣一天一天邁入老年。而多少年來,這許多醫師中,有中醫、有西醫,有信天主教的、有信基督教的,大概為我看過病的人,都成為我的好朋友。
特別是最近三、五年來,貧僧很感謝高雄長庚醫院的陳肇隆院長,他是世界知名的活體換肝專家,有「換肝之父」的美譽,也是過去佛光山大專夏令營的學員。他特地為我成立了一支十多位專業醫師的醫療團隊。他體貼我的老邁,要醫師就我,我不去就醫師,要儀器就我,不要我去就儀器,免得我舟車勞頓;甚至,他們都用卡車把儀器載到佛光山為我檢查。承蒙他的慈悲美意,實在讓我感到相當過意不去,有時候覺得比有病的負擔還要沉重。
就像美國信徒趙元修居士,他們一家族都非常誠懇熱心,特別為我安排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院作全身檢查,在盛情難卻之下,應允前往。這是一個世界知名的醫療中心,聽說許多國家的領導人、各國的公主、王子都在這裡看病。他們的檢查確實仔細,前後總共十天的診療當中,這裡的和諧、謙讓與親切,讓我深受感動,我寫下了〈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〉一文,記錄這裡的所見所聞,並且刊載在《講義》雜誌上。
儘管如此,看著信徒一家人為我奔波勞動,不得休息睡覺,聽說還花了幾十萬美金醫療費,讓貧僧感到寧可以病痛,也不要浪費他們的金錢、情意。後來,他們又有好幾次鼓勵我再去檢查,想到貧僧這個老朽之身,實在不值得他們這樣耗費精力,也就婉謝他們的好意,堅持不再去了。
二年前,在一次重感冒之後,長庚醫院幾位醫生在佛光山開山寮為我看診,強迫我一定到醫院做一次核磁共振和超音波的檢查。其實這在過去,已有過多次的經驗,過程也只是受一小時到半小時的折磨而已,沒有感到是好是壞,貧僧也沒有過問結果,就好像這個色身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樣,對它並不特別關心。因此,像醫生每次檢查後,總要做的一些說明,我聽不懂,也不想要聽,大部分都是由慈惠法師幫我聽,我想,幾十年下來,他應該聽成具備各種醫藥常識的專家了。
但這一次,醫生們神情緊張,非得要貧僧去醫院做更精密的檢查。記得那是在一間醫療室裡,十幾名醫護人員圍著我,過程中,一下子這個人要我這樣,一下子那個人要我那樣,一會兒是提手,一會兒是抬腳,這時候翻過來,那時候又轉過去;我心想,橫豎自己也看不到,就聽任他們的安排,統統照做。我知道他們的好意是為了對身體每一個部位做仔細檢查,但在我,忽然感覺到,過去的屠宰場殺豬宰牛,也不過就是這樣吧。
我不禁感慨,人生不就是如此嗎?生死存亡一線間,每個人面對老病死生都是平等的,到了最後,什麼功名富貴、權力地位,沒有什麼大不了,也不值得去恐怖畏懼了。
因此,貧僧這一生的疾病,可以說也是經常有之;因為不介意,「與病為友」這個想法,讓自己雖有病痛,還不致於如臨大敵,倒也相安無事,過得很順利。如今年近九十,生死早已置之度外,這大概與貧僧從青少年起,就在苦難歲月裡成長,覺得世間也不是怎樣美好、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有關吧!
而在佛教裡,死亡也不是沒有去處,在我們的看法,死亡不是消滅,而是像移民一樣,所謂「往生」,就是從此處移民到彼處;又好像汽車零件,這個零件壞了,換另外一個零件;這個身體壞了,換另外一個身體,這應該都是好事,不必那麼悲傷。
但大部分的人認為,生死是人生大事,事實上,在生命過程中,人之生也,何必歡喜?生了不久不是要死嗎?人之死也,何必悲哀?死了不是會再生嗎?所以,生生死死,死死生生,生命是不死的,是一種輪迴,是無窮無盡,看得淡泊,像春天播種,如夏秋生長,似冬天枯亡,這些轉換改變,也是一樁平常的事情而已。好比氣候有春夏秋冬,物質有成住壞空,人生有老病死生,又何必分別計較,那樣看不破呢?
因此,佛教講「生老病死」,在我的體會,應該把它改做「老病死生」。因為講「生老病死」,死了好像就沒有了;假如改成「老病死生」,生了以後會死,死了之後還會再生,生了就有希望,就有未來。
我非常欣賞一位老太太要過世的情形,國外的兒女子孫都回來圍繞在她的病榻前面,她望望子女說:「我想喝杯酒。」兒孫們為了滿老人家最後的願望,就倒了一杯酒給她喝。
喝過酒後,她又說:「我想抽根菸。」一位信仰西方宗教的兒子就說:「媽媽,你患了重病,不宜吃菸。」旁邊的兒女就說:「你不可以這樣講,媽媽歡喜要吃菸就讓她吃吧!」於是拿支菸給媽媽。
這位老媽媽在喝了酒、吃過菸之後,說了一句「人生真美」,就含笑而去了。到底她是帶著病友而去呢?還是病友陪她同去呢?這就不必深究了。
想到貧僧一生雖與病為友,但沒有罣礙,生病時,也不覺得自己生病,所謂「心無罣礙,無罣礙故,無有恐怖」,就能夠「遠離顛倒夢想」,《般若心經》實在是最好的人生觀。所以,貧僧常說的四句話:「冷不怕,怕風」,這是在大陸過冬的感受;「窮不怕,怕債」,這是貧僧童年的回憶;「鬼不怕,怕人」,這是社會歷練的教訓;「死不怕,怕痛」,應該就是貧僧現在生活最真實的寫照。
至於也有人問貧僧,既是修行人,又號稱「大師」,怎麼也會有這麼多疾病呢?其實,佛陀早就說過,修道人要帶三分病痛,才知道發道心。所以,疾病也是我們修道的增上緣,不要排除它,與病為友,才是最好。用《金剛經》的話來講:佛說有病,即非有病,是名有病。而這《金剛經》的妙義,就需要參詳,才能斷疑生信了。(2015.04.19口述完稿)二十一說之三